那里面有周杰伦的《范特西》,那张封面上的红衣少年,曾经是我们整个青春的偶像。还有孙燕姿的《风筝》,S.H.E的《美丽新世界》……更多的是些电影。《泰坦尼克号》那张,因为反复播放,上面已经有了细密的划痕;《大话西游》上下两部,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对白,我们几乎能倒背如流;还有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,吕克·贝松的名字,我最早就是从这碟片的封套上认识的。
这些光盘,是我和我的时代,共同的遗产。
记得那时候,家里刚买了DVD播放机,是个新鲜玩意儿。银色的,方方正正,前面有个会发蓝光的窗口,碟片放进去,会发出“嗡”的一声轻响,然后电视屏幕先是一蓝,接着电影公司的片头就出现了。那感觉,比现在用遥控器随便点开一个流媒体APP,要神圣得多,有仪式感得多。每一张碟片,都是我们精挑细选,从牙缝里省下零花钱,在学校门口的音像店,或者街边那些摆满碟片的小推车上买回来的。
买回来还不算,我们会像对待珍宝一样对待它们。先用柔软的布擦掉可能存在的指纹,再郑重其事地放进播放机。看电影的时候,我们是不快进的,连片尾字幕都要看完,仿佛那样才对得起花的钱,对得起这部电影。看完之后,又会小心地装回盒子里,按照购买的时间顺序,或者影片的类型,整整齐齐地码在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。那时候,那摞光盘不是“堆”,而是一座秩序井然的“图书馆”,记录着我们的品味和我们的热爱。
周末的下午,阳光懒懒地照进客厅,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,就会窝在沙发上,轮流看各自新买的碟。看到精彩处,我们会一起惊呼;看到感人处,有人会偷偷抹眼泪;看到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,我们会笑得东倒西歪,把沙发垫子扔来扔去。那时候,时间过得很慢,快乐也很简单,一张好的电影碟片,就能让我们兴奋和讨论一整个星期。
那摞光盘里,还夹着一些“另类”。有几张是英语听力光盘,是当年为了应付考试买的,塑封都没拆,现在想来,真是自欺欺人的典范。还有几张是电脑游戏安装盘,比如《仙剑奇侠传》和《星际争霸》。安装这些游戏需要反复地切换光盘,电脑光驱会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辛苦声响,我们则屏息凝神地等待着进度条走到百分之百。那时候的快乐,是需要等待和付出的。
时过境迁。电视换成了超薄的液晶屏,下面再也没有能放碟片的抽屉。DVD播放机早就不知道被收到了哪个储物间的角落,积满了厚厚的灰。我们现在看什么都用网络,手指动一动,成千上万的电影、剧集任君挑选,连缓冲都几乎不需要了。方便,是真的方便。可那种捧着一张实体碟片的踏实感,那种为一个镜头、一句台词而心潮澎湃的专注感,好像也随着那“嗡”的一声读碟声,一起远去了。
所以,这堆光盘,我就让它们在那儿堆着。
它们不只是塑料片。它们是时间的化石。每一道划痕,可能都对应着某一次全家聚精会神的观看;每一个泛黄的封面,都沉淀着一段旧日的气息;每一张碟,背后都站着几个当年一起看片的人,以及那时候年轻、对未来充满憧憬的自己。
我有时候会蹲在它们面前,随手抽出一张。手指触摸到那冰凉的、略带磨砂的碟面,记忆的闸门“轰”的一声就打开了。我仿佛能闻到那个夏天午后,空气里漂浮的西瓜的清甜;能听到老式空调运转时低沉的轰鸣;能看到父母还乌黑的头发,和朋友们毫无忧虑的笑脸。
我知道,它们占地方,不美观,而且从功能上说,已经彻底失去了意义。它们像一群固执的幽灵,徘徊在我现代化的客厅里,提醒着我一些我不想忘记的事情。
前几天,我三岁的小侄子来家里玩,指着那堆光盘好奇地问:“舅舅,这些亮亮的圆圈是什么呀?”
我愣了一下,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。在他出生的这个世界里,一切内容都存在于“云”端,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他无法理解,我们曾经需要依靠这样一个实体的、会磨损的“圆圈”,来获取故事、音乐和快乐。
我摸了摸他的头,笑着说:“这是舅舅的宝贝。”
他似懂非懂,很快就被平板电脑上的动画片吸引了回去。
我回过头,看着那堆在电视旁,在智能音箱、游戏机和新潮的摆件中间,显得格格不入的光盘。夕阳的余晖正好落在它们上面,某些碟片的反光面,闪烁起一片细碎、温暖的金色光芒。
它们不会再被播放了,但它们会一直被堆在那里。因为它们是我青春时代的“黑匣子”,记录了一段飞行中最颠簸也最精彩的航程。扔掉了它们,就好像扔掉了那一段生命。就讓它们堆着吧,那是我的“过去”在“现在”里,为自己保留的一块小小的、倔强的自留地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飞科创业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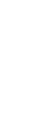 飞科创业网
飞科创业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28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28)
2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2)
3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10)
4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109)
5代买限量零食黄牛发错口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