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暖,不在掌心,而在心里。那是一种从喉咙一路熨帖到胃里,再慢慢扩散到四肢百骸的妥帖。小时候的北方小城,冬天是泼墨般的冷,风刮在脸上,像小刀子。一放学,我就成了个缩着脖子的小鹌鹑,拼命往家赶。离家巷口总有个固定的摊位,一个裹着军大衣的老爷爷,守着一个油桶改装的炉子。那炉子像个沉默的巨人,肚子里焖着轰轰烈烈的火,红薯的甜香,就从那缝隙里丝丝缕缕地钻出来,勾着人的魂儿。
我总会把攒下的几毛钱递过去,老爷爷便用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,熟练地打开炉门。一股更浓烈、更霸道的热气“呼”地扑出来,瞬间模糊了他的老花镜,也模糊了我眼前的寒冷世界。他在那堆黑乎乎、其貌不扬的“炭块”里扒拉几下,手指轻轻一按,挑出一个软乎乎的,那是熟透了的标志。他不用秤,全凭经验,递给我时总会慈祥地叮嘱一句:“丫头,小心烫着。”
我哪里等得及,双手飞快地倒腾着那块滚烫的宝贝,一边呵着气,一边迫不及待地想要撕开那层焦脆的皮。可那皮烫得很,我笨拙地抠几下,指尖就红了。这时候,爷爷总会笑着摇摇头,伸出手来,说:“来,爷爷给你剥。”
他的手,像老树皮,不怕烫。粗糙的指腹捏住红薯的一端,轻轻一撕,“刺啦”一声,那焦脆的外皮便应声裂开一道口子。他剥得极有耐心,极有技巧,不是大片地撕扯,而是顺着那裂口,一点点、一圈圈地,将那些烤得碳化的部分揭去。动作不疾不徐,像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。随着外皮的褪去,里面那层贴着薯肉的、半透明的、黏糯的“内衣”显露出来,最后,一整根完完整整、金红滚烫的薯肉便赫然呈现眼前,像一轮被小心翼翼捧出的、浓缩的小太阳。热气裹挟着近乎液态的蜜糖般的香气,蒸腾而起,扑在我的脸上。
我接过那根光溜溜、没有一点瑕疵的薯肉,一口咬下去。那是语言无法形容的满足。薯肉是烫的,甜是绵密的,带着柴火特有的烟火气,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底,所有因寒冷而生的瑟缩,都在这一口里烟消云散了。我吃得满手满脸都是黏糊糊的糖渍,爷爷就在一旁看着,眼角的皱纹笑得堆叠起来,像一朵温暖的菊花。
后来,我长大了,去了南方上大学,又留在了这座冬天湿冷入骨的城市。这里的冬天没有泼墨般的大雪,只有绵密不绝的阴雨,冷得钻心。街边也有卖烤红薯的,电烤炉,干净,却总觉得少了那股子粗粝而旺盛的生命力。我也会买,站在高楼林立的缝隙里,捧着用纸袋装着的红薯。
我也学着自己剥壳。可我的手,远不如爷爷那双树皮般的手耐烫。常常是手忙脚乱,皮剥得七零八落,薯肉也被我抠得坑坑洼洼,连带着粘上不少焦黑的皮屑。好不容易剥完,看着那残缺不全、卖相不佳的薯肉,咬上一口,甜还是甜的,暖也是暖的,可总觉得缺了最关键的一味。那口暖,到了喉咙口,就停住了,再也沉不下去,化不开周遭的寒意。
那一刻,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,当年那暖透身心的,从来不只是红薯本身。是那呼啸北风中唯一的、冒着火光的炉子;是那声“丫头,小心烫着”的乡音;是那双为我挡住所有滚烫,耐心地、一点点为我剥开坚硬外壳的、苍老而温暖的手。
那双手,为我剥开的何止是红薯的壳啊。他剥开的是整个童年的寒冬,把世间最朴素的温暖与甜蜜,毫无保留地、完完整整地呈给了我。
如今,我站在陌生的街头,捧着我自己剥的、残缺的红薯。烫手的温度从指尖传来,却再没有一双手会及时地接过去,替我承担那份灼热。风刮过来,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,就像小时候那样。可我知道,不会再有一个炉子在巷口等我了,也不会再有人,用那样温柔的动作,为我剥开一个完整的、金红的冬天了。
烤红薯还是那个味道,甜得真实,暖得具体。可我心里清楚,有些东西,就像那被撕下扔掉的、焦糊的红薯皮,永远地留在了过去。冬天年年都会来,烤红薯的香气也依旧会飘满大街小巷,只是那个帮我剥壳的人,已经不在了。
而我,必须学会自己,去面对生活里所有滚烫的、需要亲手剥开的艰难,哪怕过程笨拙,结果狼狈。只是,在每一个寒冷的黄昏,当那熟悉的香气飘来,我总会有一瞬间的恍惚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巷口,看到了那团模糊在热气后的、慈祥的笑脸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飞科创业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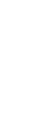 飞科创业网
飞科创业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27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27)
2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2)
3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09)
4代买限量零食黄牛发错口味阅读 (10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