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我在咖啡馆工作的第三周。本来应聘的是前台,可店里人手紧,店长拍拍我的肩说:“小伙子,试试做咖啡吧。” 我就这么被推上了咖啡机。看着别的店员手腕轻巧地晃动,洁白的奶泡在深褐色的咖啡上流淌出优雅的图案,我心里羡慕得不行,觉得那简直是魔法。
可魔法到了我手里,立刻就成了灾难。最初的几天,我连最基本的奶泡都打不好。不是打得太厚,像黏稠的奶油,根本流不动;就是打得太薄,稀拉拉像水一样,一倒进去就直接沉底。店里有位做了三年的师姐,叫阿琳,她看我手忙脚乱的样子,总会走过来轻声说:“别急,听声音。” 她把蒸汽棒插入牛奶,那种稳定的、如同撕开丝绸般的“嘶嘶”声,跟我弄出来的时断时续、要么尖叫要么沉默的噪音完全不同。我这才明白,第一步就错了。原来,打发奶泡时,蒸汽棒的喷头得刚好埋在牛奶表面之下,吸进去的空气会发出那种轻柔的“呲呲”声,太浅了全是粗泡,太深了又搅动不起来。光是找到那个“刚好”的位置,我就对着水练习了不下百次,手腕都僵了。
奶泡勉强合格后,拉花本身又是另一座大山。我第一次尝试画爱心,右手端着奶缸,左手扶着咖啡杯,双臂紧张得像两根棍子。心里默念着“融合、压低、出图”,结果手一抖,奶缸离液面十万八千里,一股白线冲进去,瞬间把浓缩咖啡的油脂撞得七零八落,最后杯子里只剩一片浑浊的灰白色。那种挫败感,真让人泄气。下班后,我常常一个人留下来,用洗洁精兑水练习,反正便宜,倒掉也不心疼。吧台上总是湿漉漉一片,映着我那张写满沮丧的脸。
转机出现在一个周二的下午。那天客人不多,我又在一次失败的尝试后,懊恼地放下奶缸。阿琳走过来,没说话,只是重新萃了一份浓缩,打了一缸奶泡。她没直接做,而是把奶缸递给我,然后站到我身后,用她的手轻轻托住了我颤抖的手腕。“感觉一下这个高度,”她的声音很平静,“不是用手臂在推,是用整个身体在送。” 那一刻,我好像突然开窍了——原来发力点不在手腕,而在沉下去的肩膀和稳定的腰腹。我第一次感觉到,奶泡不是被“倒”出去的,而是被“引导”着,像一条柔顺的丝带,自己铺展在咖啡的液面上。虽然那次最终也只是拉出了一个歪歪扭扭、不太对称的圆形,但那个圆,是我第一个能看出形状的图案!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
从那以后,我好像摸到了一点门道。我开始懂得,所谓的“爱心”,其实是从一个圆开始的。奶缸嘴在中心点靠近,流量加大,推出一个饱满的圆,然后在回收时,轻轻向前一带,划出那个尖尖的底部。而“树叶”,则是在爱心基础上,手腕需要一种轻柔而快速的左右摆动,让奶泡像钟摆一样,一层叠一层地铺开,最后收尾时,同样向前一切。这些细节,光看是看不出来的,全靠手上那一点点微妙的“感觉”。
练习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。我甚至在家里用酱油和洗洁精调出类似浓缩咖啡的颜色,继续我的“拉花大业”。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牛奶,打发了多少缸只能倒掉的奶泡。失败依然是主旋律,有时图案一边大一边小,有时叶子的纹路糊成一团。但进步的喜悦是巨大的。当我第一次独立拉出一个勉强能认出是爱心的图案时,我几乎是屏住呼吸,盯着那个杯子看了足足五分钟,才舍得让客人端走。那位客人说:“今天这个心,很暖。” 就这一句话,让我觉得之前所有的折腾都值了。
真正迎来质变的,是一个忙碌的早高峰。我像上了发条一样,连续做了几十杯咖啡,手腕已经完全放松,几乎是一种肌肉记忆在操作。轮到一杯拿铁时,我习惯性地融合、压低、摆动、收尾,一气呵成。直到把杯子放到出餐台,我才看清——那是一片脉络清晰、左右对称的树叶,它静静地躺在杯子里,优雅又自信。那一刻,周围嘈杂的声音仿佛都消失了,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:“嘿,你做到了。”
现在,我已经能稳定地做出各种图案了。但最让我珍惜的,反而不是那些最完美的作品。我珍视的是那个过程——从最初那团“被踩烂的蒲公英”,到第一个歪歪扭扭的圆,再到那片终于成形的树叶。这个过程里,有手忙脚乱的尴尬,有屡战屡败的绝望,也有灵光一现的狂喜和豁然开朗的平静。它教会我的,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,就是最简单也最实在的一件事:所有看起来的毫不费力,背后都是拼尽全力的练习。而当你终于穿越了那片迷茫与失败的迷雾,手中流淌出的,就不仅仅是咖啡和牛奶,那是一段看得见的、关于成长的印记,温热,而芬芳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飞科创业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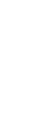 飞科创业网
飞科创业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27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27)
2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2)
3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09)
4代买限量零食黄牛发错口味阅读 (10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