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忙音,几乎贯穿了我整个少年时代,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一道无形的墙。
父亲是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家就像他的一个临时驿站。他回来,带着一身风尘和疲倦,睡上一两天,然后又消失。而我和母亲,还有这部老式的红色座机电话,就成了守候在这个驿站里的人。
母亲总是算着他大概该到哪儿了,该打电话回来了。那时候没有手机,父亲总是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,或者某个小旅馆的前台,往家里拨电话。电话铃声一响,母亲就会放下手里的一切活计,几乎是扑过去接起来。他们通话的时间通常不长,说的也无非是“到了没”、“吃饭没”、“路上小心”这些家常话。但我能看见,母亲接电话时,脸上那种紧绷的神情会瞬间松弛下来,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。
而我,总是在一旁假装看书或者看电视,耳朵却竖得老高,捕捉着他们的每一句对话。我渴望父亲在最后会说一句:“让儿子来接一下电话。” 可是,十次有九次,等来的都是母亲放下电话后,对我说:“你爸让你好好学习。”
后来,我渐渐不满足于这种间接的交流。我开始尝试主动给父亲打电话。我知道他大概的行程,估摸着他应该到了某个地方,安顿下来了,就会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,拨通那个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第一声忙音响起,我的心跳会莫名加速,脑子里飞快地组织着语言:该说什么?先叫“爸爸”?还是直接说“是我”?问他累不累?还是告诉他我这次考试考得不错?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第二声,第三声……无人接听。他可能还在卸货,可能在洗澡,也可能在路边小馆子吃饭。我那点鼓起的勇气,在一声声平稳的忙音里,像被针扎破的气球,慢慢瘪了下去。我会紧紧握着听筒,仿佛那样就能把遥远的他拉近一些。手指绕着卷曲的电话线,一圈,又一圈,直到指尖发白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第五声,第六声……希望越来越渺茫。我开始胡思乱想,是不是我记错时间了?是不是他出车去了别的地方?那种等待,是一种微小的、持续的煎熬。你能感觉到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,而你和你想联系的那个人之间,隔着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千山万水,还有这冰冷的、无法逾越的“嘟嘟”声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咔。”
通常是七声之后,电话会自动挂断,听筒里会变成一种短促而尖锐的“嘟、嘟、嘟”的断线音。那声音像是一个最终的判决,宣告了这次联络的失败。我慢慢地、失落地放下听筒,那“咔哒”一声轻响,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这种由期待到失落的过程,重复了太多次。以至于那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忙音,在我听来,不再是简单的声音,它变成了一种感觉。是空荡荡的房间,是窗外漆黑的夜色,是心里那种没着没落的牵挂,还有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。我和父亲之间,本来话就不多,这反复失败的沟通尝试,好像让我们的距离更远了。我觉得他并不想接到我的电话,或者说,我的存在,在他的奔波劳碌里,并不那么重要。
有一次,是个冬天的晚上,外面下着大雨。母亲上夜班,家里就我一个人。我听说父亲那天会到A城,一个以路况险峻出名的地方。风雨敲打着窗户,呜呜作响。我看着钟,越来越担心。九点,十点……他应该早到了。我忍不住拨通了他的电话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忙音混着窗外的雨声,显得格外漫长和清冷。一声,两声……我数到第十声,没有人接。一种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。我挂了,又拨。还是忙音。那天晚上,我记不清自己拨了多少次,直到后来握着听筒,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第二天早上,是电话铃声把我吵醒的。是父亲。他的声音带着沙哑和疲惫,但很平静。他问我昨晚是不是打电话了,说他的车在半路抛锚了,在修理厂待了一夜,刚回到旅馆。我“嗯”了一声,想说很多话,想问他在哪里抛锚的,冷不冷,怕不怕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最后只挤出一句:“没事,就是问问你到了没。”
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,然后说:“到了。没事。你好好上学。”
那一次之后,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那忙音,并非只意味着无人接听。它也可能意味着,他正在风雨里抢修轮胎,正在崎岖的山路上聚精会神地开车,正在为了我们这个家,扛着所有的艰辛。而我在这边听到的寂寞和委屈,他在另一边,或许正用汗水和危险承担着。
后来,我上了大学,离开了家。手机开始普及,那部红色的座机电话渐渐被淘汰。我和父亲也都有了手机,联系变得无比便捷,随时可以打电话,发短信。奇怪的是,我们通话的次数并没有增加多少,内容也还是那些简短的问候。但那种因为“忙音”而产生的焦虑和隔阂,却慢慢消散了。因为我长大了,我理解了他当年的沉默和奔波。
很多年后的一个下午,我在整理老家的杂物间,又看到了那部蒙尘的红色电话机。我下意识地把它拿到客厅,接上了电话线。令我惊讶的是,线路居然是通的。我随手拨了一个空号。
“嘟——嘟——”
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忙音,再次响起。
一瞬间,时光仿佛倒流。我好像又变回了那个趴在沙发上,紧张地握着听筒的少年,心里充满了小心翼翼的期待和害怕落空的忐忑。窗外还是那样的阳光,空气中仿佛还弥漫着母亲做饭的香味,而那个跑长途的父亲,仿佛下一刻就会在某个遥远的电话亭里,接起我的电话。
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原来,这冰冷的忙音,早已在不知不觉中,成了我青春记忆里一个独特的注脚。它不仅仅是等待和失落,它更是一根看不见的线,线的这头,是家,是不断长大的我;线的那头,是路上,是日渐老去的父亲。我们都不善于表达感情,所有的牵挂、担忧、以及那份深沉的、从未说出口的爱,都藏在了这一声接一声的“嘟——嘟——”里。
它曾经是我以为的隔阂,最终却成了我理解的桥梁。
我轻轻放下听筒,那忙音似乎还在耳边回荡。但这一次,我心里不再有空落,而是被一种温暖而酸楚的情绪填得满满的。我拿出手机,拨通了父亲的号码。这一次,只响了一声,就接通了。
“爸,”我说,声音有点哑,“晚上回家吃饭吗?我买了你爱吃的鱼。”
电话那头,父亲愣了一下,随即传来他带着笑意的声音:“好,我早点收车回来。”
你看,我们终于不再需要那漫长的忙音来传递思念了。但我会永远记得它,记得它曾如何陪伴了一个孩子的成长,又如何见证了一个父亲沉默的担当。那声音,是时代的印记,更是我和父亲之间,一段独特而深情的密码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飞科创业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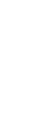 飞科创业网
飞科创业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27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27)
2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2)
3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09)
4代买限量零食黄牛发错口味阅读 (10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