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下午三点十二分,调度室的电话又响了,那铃声像根针,总能一下子扎进人心里。“老张,城西幸福小区,有个老爷子心梗,情况危急,家属已经急得不行了。”我撂下喝了一半的茶水,抓起钥匙就往外冲。那茶水,是徒弟小王刚给我泡的,还烫着嘴,但我一次也没能安安稳稳喝完过。
跳上车,点火,拉响警笛,这一套动作我闭着眼睛都能完成。警笛声“呜哇—呜哇—”地响起来,像扯着嗓子在喊:“让让!快让让!”车子冲出医院大门,汇入午后略显拥挤的车流。阳光有些晃眼,我眯缝着眼,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,手心有些湿漉漉的。
副驾上的医生老李和护士小刘已经迅速进入状态,检查着设备。老李是个老资格了,话不多,但眼神沉稳,有他在,我心里就踏实几分。小刘虽然年轻,但手脚麻利,心也细。我们三个,算是个老搭档了。
车子在车流里穿梭,像一条急于归巢的鱼。我死死盯着前方,大脑飞快地判断着每一寸空隙。鸣笛声一刻不停,它不只是声音,它是我手里的武器,是我为车里那个还没见面的病人,争取时间的第一道工具。
我看到前面的车,有的听到警笛,会下意识地顿一下,然后赶紧向旁边靠,给我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。每当这时,我心里都会默默念一句:“谢谢,谢谢了!”真的,这份情我记着。但也有的车,不知道是没听见,还是没在意,依旧不紧不慢地开着,占着道。那时候,我心里就跟火烧一样,恨不得自己能长出一对翅膀飞过去。我只能更用力地按喇叭,用变换的警笛声催促,寻找任何一个可能超车的机会。有时候逼不得已,压着实线过去了,后视镜里看到摄像头闪了一下,我心里也只能苦笑:“扣分就扣分吧,救人要紧。”
抢出这几分钟,可能就意味着生的希望。这个道理,不用别人讲,我每次握上方向盘,就刻在骨头里了。
赶到幸福小区时,老远就看到几个人在楼下焦急地挥手。我们把担架车推下来,跟着家属一口气跑上五楼。门开着,屋里一股压抑的气氛。那个老爷子躺在沙发上,脸色蜡黄,嘴唇发紫,捂着胸口,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。他老伴儿在一旁抹眼泪,看见我们像看见了救星,抓着老李的手直哆嗦:“医生,求求你们,快救救他……”
老李和小刘立刻上前检查,测血压,做心电图,情况确实不好,急性心肌梗死。必须马上回医院进行溶栓或者手术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老爷子挪到担架上,固定好。下楼是件麻烦事,老旧的楼梯又窄又陡,我和老李一前一后,紧紧抓着担架,小刘在旁边扶着输液瓶,一步一挪,生怕有一丝颠簸。老爷子很轻,但我感觉手里的担架有千斤重。
终于把病人安全抬上车。车厢门“哐当”一关,仿佛把外面的世界隔绝了。车里瞬间成了一个移动的抢救室。小刘麻利地给老爷子吸上氧气,接上心电监护仪。那“嘀嘀、嘀嘀”的声音,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、刺耳。老李一边准备着急救药品,一边通过话筒跟我保持沟通:“老张,稳着点开,病人情况不稳定,心率下来了!”
“明白!”我应了一声,深吸一口气,再次拉响警笛,挂挡,给油,车子又一次汇入车流。
回去的路,感觉比来的时候更漫长。心电监护仪那“嘀嘀”的声音,通过话筒隐约传到我耳朵里,它成了我心跳的节拍器。那声音规律,我的心就稍安;那声音要是有个停顿或者变调,我的心就能瞬间提到嗓子眼。后视镜里,我能看到老李和小刘忙碌的身影,他们额头上都是汗,但眼神专注。
有一段路特别堵,几个红绿灯路口排起了长龙。警笛声在密集的车流中显得有些无力。我看着前面蠕动的车辆,心里急得不行。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,那都是老爷子的命啊!我忍不住拿起对讲话筒,几乎是吼出来的:“老李,怎么样?”
隔了几秒,老李沉稳的声音传来:“还在坚持,血压有点低,正在用药。老张,别慌,安全第一,但我们确实需要快点。”
“好!你们稳住!”我放下话筒,瞅准对面车道一个空当,猛地一打方向盘,冲了过去,耳边能听到其他车辆紧急刹车的刺耳声音。我也顾不上了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“快!快!快!”
风从车窗缝隙灌进来,吹在我脸上,我才发觉自己也是一头的汗。我不怕违章,不怕罚款,甚至不怕出事,我就怕听到后面说“老张,不用急了……”这种话,我听过,那滋味,一辈子都不想再尝。
终于,医院那熟悉的白色大楼出现在视野里。我提前用对讲机和急诊中心联系好了,车子刚冲进医院大门,就看到绿色通道入口处,几个医护人员已经推着平车等在那里了。
一个精准的刹车,车子稳稳停住。我跳下车,和医护人员一起,迅速将老爷子转移到平车上。看着他们推着平车,一路小跑着冲进急诊大厅,冲进抢救室,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,才稍微往下落了落,但并没有完全放下。
我关掉警笛,世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安静得让人有点不适应。我靠在车身上,点了一支烟,手有点抖,吸了一口,烟雾缭绕中,才感觉浑身的力气像被抽走了一样。车厢里还残留着消毒水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药物的气息,老爷子躺过的地方,担架床单有些凌乱。
过了一会儿,老李和小刘也从抢救室出来了,摘下口罩,脸上带着疲惫。我递过去两支烟,老李摆摆手,小刘则靠在一边喝水。
“怎么样?”我问,声音有点沙哑。
老李吐出一口烟圈:“送来得还算及时,溶栓药用了,情况暂时稳住了,接下来看血管通得怎么样,可能还要准备手术。算是从鬼门关暂时拉回来一只脚。”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这才感觉后背的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。小刘笑着说:“张师傅,您今天开得可真够猛的,我差点没站稳。”
我苦笑一下:“不猛不行啊,这抢回来的,可能就是一家人往后的日子。”
我们都没再说话,默默地收拾着车厢,补充消耗掉的氧气和药品,为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起的铃声做准备。这就是我们的工作,一场接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赢了,不一定有掌声;输了,可能就是一条生命的逝去和一个家庭的破碎。
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是前年冬天的一个深夜,也是接到一个心梗的求救。病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,家里的顶梁柱。那天路况特别差,刚下过雪,路面结了一层薄冰。我开得小心翼翼,但速度怎么也提不起来。警笛在寂静的雪夜里传得很远,但前方的车辆让行变得比平时迟缓。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能感觉到时间在指尖一点点溜走。
赶到他家时,人已经意识不清了。在回医院的路上,我听着后面医生护士紧张的抢救声,心电监护仪那刺耳的、拉成一条直线的长鸣声最终还是响了起来……那声音,像一把冰冷的锥子,至今还扎在我心里。车开到医院,医生宣布死亡,他妻子那一声绝望的哭喊,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她瘫坐在地上,一遍遍地问:“为什么不能再快一点?为什么……”
那一刻,我靠在冰冷的救护车上,看着漫天飘落的雪花,感觉自己无能透了。我恨那天的天气,恨那些没有及时让路的车,更恨自己,为什么不能再快一点。那种无力感和愧疚感,缠绕了我很久很久。
所以,我现在每一次出车,每一次鸣笛,每一次在车流中穿梭,都带着一种“赎罪”般的心情,都想着那个雪夜和那个女人的哭声。我告诉自己,只要有一线希望,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,我就必须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我这双手握着的,不只是方向盘,更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,是一个个家庭的圆满。
收拾完车厢,我坐回驾驶室,把那杯已经凉透的茶水喝完,滋味苦涩,却让我清醒。夕阳的余晖透过车窗,落在副驾的座位上。对讲机安静地待在那里,我知道,这份安静是短暂的。也许下一秒,它又会尖锐地响起,而我和我的伙伴们,会再次跳上车,拉响警笛,冲向另一个需要我们的地方,去进行下一场生死时速的争夺。
这条路,我还会继续开下去。只要警笛还能响起,只要还有需要我的人,我就会一直开下去,尽我所能,快一点,再快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飞科创业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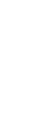 飞科创业网
飞科创业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27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27)
2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12)
3网上买薯片,收到后袋子漏气阅读 (109)
4代买限量零食黄牛发错口味阅读 (107)
5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